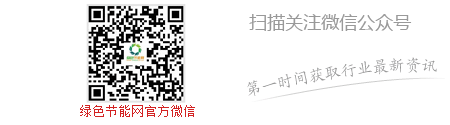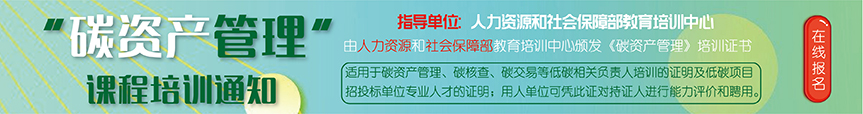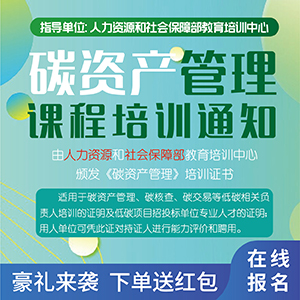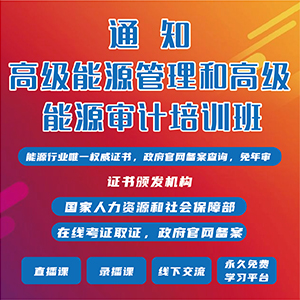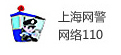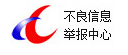|
| 中國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針對光伏產業的“雙反”只是美國保護主義大貿易大潮的開始,等待中國的將是更加復雜和激烈的市場博弈,“狹路相逢,勇者勝”。 |
拉鋸了近半年時間的中美光伏“雙反”博弈標志著中美在新能源領域的鏖戰剛剛開始。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盡管美國進口需求很強勁,但中國企業在美銷售的光伏產品價格,一年內下降了40%,美國多家光伏企業遭遇銷售下滑的重創接連倒閉,并驚動了美國政商兩界。Solarworld等美國7家光伏生產商聯名上書,要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及美國商務部制裁中國光伏企業的“傾銷”行為,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主席亨利則表示,“美國正面臨失去清潔能源領導地位的危險”。
美國上訴光伏企業在破產聲明中,都將公司崩潰歸咎于全球需求下降及競爭過于激烈,特別是來自中國同行的競爭。美國光伏企業被中國光伏企業打敗了,這讓一直將清潔能源技術作為重振美國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并通過投資稅收減免、貸款擔保、出口補助金等一系列措施為光伏產業提供支持的奧巴馬著實十分懊惱,要知道,新能源產業可是奧巴馬推行“再工業化”經濟戰略的重心所在。
“再工業化”并非一個新概念,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泰•埃茲厄尼提出。詹姆斯•米勒在回顧美國產業演進和1973年產業衰退的基礎上,指出,“再工業化”作為一種積極的產業政策選擇,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推動產業調整和升級的,以提升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20世紀80年代,鑒于日美制造業的競爭格局逆轉,美國里根政府提出了恢復制造業地位的主張。羅伊•羅斯維爾和威特•杰格維爾德把“再工業化”定義為產業結構的轉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資產更新換代,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但從性質來看,當前美歐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絕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超出了“再工業化”的范疇,向新的產業革命邁進。2008年的金融危機幾乎摧毀了美國幾十年來的發展模式,以透支消費、信貸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繁榮為支點的美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危機后的美國經濟何去何從?這是奧巴馬政府必須解答的難題。聯合國工發組織的統計數字顯示,近10年來,全球制造業總量中,美國份額不低于1/5,但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卻在逐年下降。美國需要改變過去那種“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
為此奧巴馬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預計美國出口將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長,5年后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將超過3萬億美元,然而,15%的增長似乎遙不可及,因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低端制造業已經大部分從國內轉移出去,而其高端制造業的成本相對較高,歐洲、日本和韓國都是美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2001年至2009年,美國出口額的平均增長率是4.1%,這與15%的增長率相差懸殊。從勞動力成本和勞動生產率的比較優勢來看,相對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美國制造業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備優勢。
因此,美國深知只有通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帶動新一輪產業周期,奧巴馬不僅將發展新能源產業作為轉型手段,更是作為應對經濟危機、拉動國內就業、促進“節能減排”的重要途徑。為此,奧巴馬政府通過大規模的財政補貼來支持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根據中國光伏聯盟調查顯示,美國多個州通過各種扶持政策不斷對美國多晶硅公司進行補貼。例如,2010年,Hemlock公司和REC公司獲得上億美元政府補貼,享受補貼電價甚至低于聯邦平均電價水平。
整體經濟轉型之中的中國同樣將新能源產業作為中國轉型和結構升級的引擎所在。金融危機后在新興產業振興規劃的推動下,包括光伏產業在內的新能源產業出現了爆發式增長。
目前中國產品在可再生能源市場中越發地占據主要地位,2010年中國光伏產量已達16GM-17GM,占據全球半壁江山。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而言,中國太陽能電池等光伏產業還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中下游,競爭形勢日趨激烈。尤其是越往下游(組件生產、太陽能應用產品)競爭越激烈,主要是由于下游產品生產投資少、建設周期短、技術和資金門檻低、最接近市場,因此也造成了中國光伏產業的產能過剩,更易受到外部沖擊。
去年以來,外部需求大幅萎縮造成光伏產品價格急速下滑,多晶硅電池企業出現大面積虧損。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硅業分會最新統計顯示,國內40多家多晶硅企業除6至7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已陷入全面停產狀態。
令人擔憂的是,現在看來,對新能源的市場需求已經趨于飽和,但各國都要在有限的市場資源中獲得更大的份額,自然不可避免的要“短兵相接”。美國已經確定把新能源產業作為其實現“再工業化”和重塑美國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而中國也必須完善光伏產業配套體系建設,加快主要核心技術和裝備制造技術的升級,重新奪回并開拓更為廣闊的市場。
中國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針對光伏產業的“雙反”只是美國保護主義大貿易大潮的開始,等待中國的將是更加復雜和激烈的市場博弈,“狹路相逢,勇者勝”。